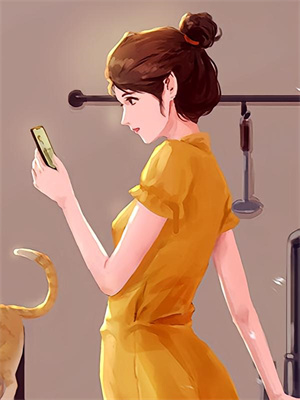简介
今天要推的小说名字叫做《同看星辰》,是一本十分耐读的青春甜宠作品,围绕着主角苏星辰顾辰光之间的故事所展开的,作者是西红柿打蛋汤。《同看星辰》小说连载,作者目前已经写了176194字。
同看星辰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周二下午的教师办公室里弥漫着茶水、粉笔灰和陈年纸张的气味。
苏星辰和顾辰光一左一右站在陈老师的办公桌前,像两个等待宣判的被告。窗台上的绿萝长得茂盛,藤蔓垂下来,在下午四点的阳光里投出细碎的影子。陈老师不紧不慢地泡茶,陶瓷杯盖碰撞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“坐。”她指了指面前的两把椅子。
星辰坐下来,背挺得笔直。顾辰光没有动,双手在校服裤兜里,目光落在窗外场上踢球的学生身上。他整个人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。
“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?”陈老师端起茶杯,吹了吹水面上的茶叶。
“互助小组。”顾辰光的声音很平,平得像数学试卷上的标准答案,“我反对。这种安排没有效率。”
“效率?”陈老师笑了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,“顾辰光,你的人生字典里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字?”
顾辰光没有回答。阳光在他的眼镜框上反射出两个小小的、刺眼的光斑。
“苏同学呢?你怎么想?”陈老师转向星辰。
星辰的手指在膝盖上绞在一起。她想起早上数学课上顾辰光那张纸条——“透视法适用于视觉艺术,不适用于数学证明”,想起他转笔时精确的节奏,想起他桌上那个折得一丝不苟的纸飞机。她想起母亲常说:艺术家和数学家是世界的两种极端,一个用感觉触摸永恒,一个用逻辑证明永恒。
“我……”她开口,声音有点,“我觉得不太合适。我和顾同学……思维方式不太一样。”
“就是因为不一样,才要互相学习。”陈老师放下茶杯,从抽屉里抽出两张试卷,平铺在桌面上。
一张是数学卷,右上角用红笔写着醒目的“150”。星辰认得那是顾辰光的字迹——每个数字都写得工整,就像印刷体。另一张是语文卷,作文栏里用潇洒的行书写着“45”,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修改符号。
“这是你们上周模拟考的卷子。”陈老师说,“顾辰光,你先看看苏同学的作文。”
顾辰光这才勉强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,低头看向那张语文卷。作文题目是《记忆中的光》。星辰的字不算好看,但很有特点,笔画间带着绘画的韵律感。她写的是母亲教她看星星的那个夜晚:
“……母亲说,每一颗星星都是一封来自过去的信。光在宇宙中走了几百年、几千年,才抵达我们的眼睛。所以我们看见的不是星星现在的样子,而是它几百年前、几千年前的样子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记忆也是这样——我们记得的永远不是事情本身,而是它发出的光,经过时间的漫长旅行后,最终抵达心灵的模样……”
顾辰光的目光在那段文字上停留了很久。久到星辰以为他睡着了,或者灵魂出窍了。但他只是站着,一动不动,像一尊雕塑。阳光在他侧脸上移动,照亮了他下巴上一道很淡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疤痕。
“你母亲是做什么的?”他突然问,声音很轻。
星辰愣了一下:“她……以前是画家。后来转行做了科研。”
“什么方向?”
“光学材料。她说她想研究出能留住光的材料。”星辰顿了顿,“但她去世了,三年前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窗外的喧闹声突然变得很遥远,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陈老师端起茶杯,又放下,陶瓷底座在木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磕碰声。
顾辰光终于抬起头。他看着星辰,镜片后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流动,很慢,很深,像深秋的湖水。
“我母亲也是科学家。”他说,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,像在背诵一道复杂的证明题,“高能物理。她研究宇宙中的基本粒子。她说,如果我们能找到最小的粒子,就能理解最大的宇宙。”
星辰屏住呼吸。
“她也去世了。五年前,实验室事故。”
陈老师轻轻地叹了口气,声音轻得像一声耳语。
顾辰光重新低下头,继续看试卷。后面的评语是陈老师写的:“情感真挚,描写细腻,但逻辑结构松散,论证不够严谨。建议多学习议论文的基本结构。”
“情感真挚。”顾辰光重复这四个字,像在品尝某种陌生食物的味道,“但逻辑结构松散。”
“现在看看你的数学卷。”陈老师说。
星辰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数学试卷上。最后三道大题,她写了思路,但没算完。在最后一道立体几何题的空白处,她画了一个小小的锥透视图,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从A点看,这个角应该更锐利一些。”
顾辰光的指尖在那个透视图上轻轻拂过。他的手指很白,指甲修剪得整齐净,指腹有写字磨出的薄茧。
“你用了视觉拆解法。”他说,不是疑问,是陈述。
“我不太会套公式。”星辰小声说,“但我能‘看见’图形在空间里的样子。”
“能看见?”顾辰光终于转过头,第一次真正地看着她。不是看一个同桌,一个同学,一个麻烦。而是看一个……一个存在。“你是说,你能在脑子里构建三维模型?”
星辰点点头:“我妈妈教我的。她说画画的人要有‘空间感’,就像数学家要有‘数感’一样。”
顾辰光没说话。他拿起那张数学卷,走到窗边,对着光看。阳光透过纸张,把星辰画的那些透视辅助线照得发亮,像某种神秘的符咒。
“所以你在考场上,不是不会做。”他背对着她们,声音从阳光里传来,“你是在脑子里,把这些几何体转来转去,找一个最好的观察角度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然后你发现,从这个角度拆解,计算量会减少一半。”
“……对。”
顾辰光转过身。逆着光,他的脸在阴影里,只有眼镜框的边缘闪着金色的光。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?”他问。
星辰摇摇头。
“这是天赋。”他说,声音里有种奇怪的紧绷感,“未经训练的空间想象天赋。如果你学会用数学语言描述它,你会是顶尖的几何学家。”
办公室里再次安静下来。这次安静里有种不同的质地,不再是对峙,而是一种……探测。像两个探险家在黑暗的洞里,用火把照亮彼此的脸,发现对方来自同一个方向。
陈老师适时地开口:“所以你们明白了吗?顾辰光,苏星辰能教你如何用‘感觉’理解世界。苏星辰,顾辰光能教你如何用‘逻辑’表达感觉。你们是彼此的镜子。”
她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表格,推到两人面前。那是“文理互助小组结对确认表”,下面有签名栏,还有一行小字:“每周二、四下午四点至五点,图书馆三楼A区。至少持续一学期。”
“签吧。”陈老师说,语气温柔,但不容拒绝。
星辰拿起笔。笔尖悬在纸上,墨迹在空气中颤抖。她看向顾辰光。他还站在窗边,手里捏着那张数学卷,纸张的边缘被他捏出了细小的褶皱。阳光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光晕,尘埃在那个光晕里缓缓旋转,像一个小小的星系。
“如果我拒绝呢?”顾辰光问,没有回头。
“那就没有期末的素质评价加分。”陈老师的声音依然温和,“而且,我会每天放学后单独给你补语文,直到你的作文能写出‘情感’为止。”
顾辰光的肩膀几不可察地绷紧了。他讨厌计划被打乱,讨厌浪费时间,更讨厌被强迫。星辰几乎能听见他脑子里齿轮高速转动的声音——计算利弊,分析得失,寻找最优解。
五秒钟后,他走回桌边,拿起笔,在表格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字迹凌厉,笔画如刀。
苏星辰。顾辰光。
两个名字并排写在纸上,中间隔着一段尴尬的空白。一个潇洒飘逸,一个工整冷硬。就像他们本人。
陈老师满意地收起表格:“明天开始。图书馆三楼A区,靠窗的座位已经给你们留好了。”她顿了顿,看向星辰,“对了,苏同学,你母亲……苏婉,她是不是曾经在江大艺术学院任教?”
星辰的心脏猛地一跳:“您怎么知道?”
“我听过她的讲座。”陈老师靠回椅背,目光变得悠远,“很多年前的事了。她讲‘艺术中的数学之美’,用分形几何分析梵高的《星月夜》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数学和艺术可以离得那么近。”
星辰的手在桌子下面握紧了。指甲陷进掌心,带来清晰的刺痛感。
“您还记得……讲座的具体内容吗?”
“记得一些。”陈老师端起茶杯,氤氲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,“她展示了一些很特别的手稿,是数学公式和绘画草图的结合。她说她在做一个跨学科研究,和一位物理学家,想找到某种……”她顿了顿,似乎在回忆确切的词,“某种‘通用语言’,可以同时描述美和真理。”
顾辰光突然抬起头:“那位物理学家叫什么?”
陈老师看了他一眼,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,像怜悯,像惋惜,像某种深埋了很久的秘密终于要破土而出。
“姓顾。”她轻声说,“顾明华教授。很巧,不是吗?和你同姓。”
空气凝固了。
窗外的喧嚣——哨声、奔跑声、篮球落地的砰砰声——突然全部消失了。世界变成了一幅静物画:阳光斜射,尘埃悬浮,绿萝的叶子静止不动,茶杯口的热气笔直上升。星辰听见自己的心跳,一下,两下,沉重得像敲钟。她看见顾辰光的脸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,白得像纸。他镜片后的眼睛睁大了,瞳孔收缩成两个小小的、黑色的点。
“您是说,”他的声音嘶哑,像砂纸磨过金属,“我母亲,和苏星辰的母亲,曾经是同事?”
“伙伴。”陈老师纠正道,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今天天气不错,“至少在我听讲座的那个时候是。后来……我就不清楚了。”
她站起身,走到档案柜前,拉开最底下的抽屉,翻找了一会儿,抽出一本相册。相册的封面是深蓝色的,边角已经磨损。她翻开其中一页,推到两人面前。
那是一张黑白照片,有些年头了,边缘已经泛黄。照片上是两个年轻女性,并肩站在一栋老式建筑前。左边那个长发披肩,穿着碎花连衣裙,手里拿着一卷画纸,笑容灿烂得像盛夏的阳光——是年轻的苏婉。右边那个短发利落,白衬衫,黑裤子,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,表情严肃,但眼神里有光——是顾辰光的母亲,顾明华。
她们身后,建筑的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:“交叉学科研究中心”。
“这是她们的启动仪式。”陈老师用手指轻轻抚摸照片边缘,“那大概是……八年前?苏婉老师还没离开艺术学院,顾教授也还在国内。她们说要一起做一件‘改变世界认知方式’的事情。”她笑了笑,笑容里有些苦涩,“年轻人总是有很多宏大的梦想。”
星辰盯着照片,盯着母亲年轻的脸。她记得母亲,但记忆里的母亲总是带着疲惫,眼底下有淡淡的青黑,笑容也总是很浅,像隔着一层雾。而照片里的母亲,笑得那么亮,那么无所顾忌,像从来没有受过伤,从来没有失去过什么。
“她们研究什么?”顾辰光问。他已经恢复了平静,声音回到了那种没有起伏的调子,但星辰看见他的手在桌子下面握成了拳,指节发白。
“具体内容我不知道。”陈老师合上相册,“那是个保密。但苏婉老师在讲座里提过一句,她说她们在寻找一种方法,‘把星光变成文字,把公式变成图画’。”她摇摇头,“很诗意的说法,对吧?可惜……”
可惜什么,她没有说下去。但星辰知道。可惜三年前,母亲在实验室里倒下,再也没有醒来。可惜五年前,顾明华教授在一次实验事故中去世。可惜两个想要“改变世界认知方式”的人,一个离开了,一个转行了,然后都离开了。
“所以,”陈老师重新坐回椅子上,目光在两人脸上来回移动,“现在你们明白了吗?我让你们组成互助小组,不只是为了提高成绩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变得更轻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:
“也许你们可以从对方身上,找到一些你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答案。”
放学铃响了。尖锐的铃声划破寂静,像一把刀切开了凝固的时间。窗外的喧嚣重新涌进来,填满办公室的每个角落。尘埃又开始在阳光中飞舞,绿萝的叶子在微风里轻轻摇晃。
顾辰光第一个站起来。他背起书包,动作有些僵硬,像关节生了锈的木偶。
“明天下午四点,图书馆三楼。”
他说完,没有看星辰,也没有看陈老师,径直走出了办公室。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,由近及远,最终消失在楼梯的拐角。
星辰还坐在那里,盯着桌上那张合影。照片里的两个女人并肩笑着,年轻,明亮,充满希望。她们不知道八年后,一个会躺在冰冷的墓碑下,一个会在病床上握住女儿的手,轻声说“对不起,星星,妈妈不能陪你去看更大的世界了”。
“苏同学。”陈老师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。
星辰抬起头,发现陈老师的眼睛有些湿润。她摘下眼镜,用衣角擦了擦镜片。
“有时候,”陈老师重新戴上眼镜,镜片后的眼睛显得格外大,格外深,“命运会用很奇怪的方式,把断开的东西重新接起来。我们不知道那是好是坏,但……”她停了一下,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,“但至少,那是一种完整。”
星辰慢慢地站起来,背起书包。画具箱很沉,压得她肩膀发疼。她走到门口,手放在门把上,冰凉的金属触感让她清醒了一些。
“陈老师,”她没有回头,“您今天告诉我们这些,是为了什么?”
身后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星辰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
“为了不忘记。”陈老师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很轻,很疲惫,“也为了……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有些问题,如果不去问,就永远不会有答案。有些人,如果不去了解,就永远只是陌生人。”
星辰推开门。走廊里空荡荡的,夕阳把一切都染成金色。她一步一步往前走,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。经过高二(3)班教室时,她下意识地朝里看了一眼。
顾辰光的座位是空的。桌面上什么也没有,净得像从来没有人坐过。只有那支笔,那本习题集,还有那个纸飞机,还放在桌子正中央,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。
但星辰注意到,纸飞机的机翼上,那个等边三角形旁边,多了一行很小很小的字。小得像蚂蚁,但她还是看见了——
“为什么?”
铅笔写的,字迹很轻,很细,像一声叹息,像一个问题,像一个开始。
星辰站在那里,看了很久。直到夕阳沉到教学楼后面,天空从金色变成深蓝,第一颗星星亮起来。
她想起母亲说过的话。
“星星是天空的伤口,也是光亮的来处。”
她背起画具箱,转身走下楼梯。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,一声,一声,像心跳,像倒计时,像某种不可逆转的东西已经开始转动。
而在三楼的教师办公室里,陈老师还坐在桌前。她重新翻开那本相册,看着照片上两个年轻的女人,手指轻轻拂过她们的脸。
窗外,夜色渐浓。
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,在深蓝色的天幕上,像散落的钻石,像未写完的诗句,像等待被解答的谜题。
而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,顾辰光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他没有开灯,就坐在黑暗中,手里拿着那本被颜料染过的笔记本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,落在翻开的页面上。那些蓝色的污渍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,像星空,像深海,像所有无法言说的、沉默的、悲伤的东西。
他伸出手指,轻轻触摸那行褪色的小字——
“给阿辰——妈妈”
指尖下的纸张粗糙而脆弱,像蝴蝶的翅膀,像逝去的时光,像所有一碰就会碎的东西。
然后,很轻地,他把额头抵在笔记本上,闭上了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