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充满奇幻与冒险的古风世情小说,那么《昨日明月照今我》将是你的不二选择。作者“雾峪风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林晚音的精彩故事。目前这本小说已经完结,最新章节第14章,喜欢这类小说的你千万不要错过!主要讲述了:白云观的山门,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,像一头沉默的巨兽,伏在西山山腰。马车在离山门还有一里地的岔路口停下。苏明真跳下车,把缰绳拴在一棵老松树上,回头压低声音:“不能走正门。今儿夜里观里也不太平,我看见好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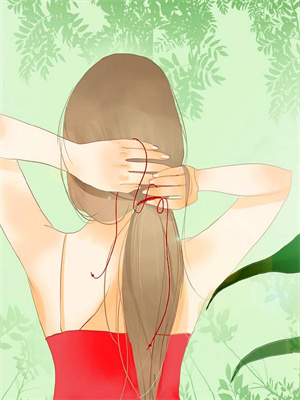
《昨日明月照今我》精彩章节试读
白云观的山门,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,像一头沉默的巨兽,伏在西山山腰。
马车在离山门还有一里地的岔路口停下。苏明真跳下车,把缰绳拴在一棵老松树上,回头压低声音:
“不能走正门。今儿夜里观里也不太平,我看见好几拨人上去,有官差打扮的,也有便衣,眼神都带着钩子。”
我心里一沉。果然,连白云观也被盯上了。
“走后山。”林晚照忽然开口。他不知何时已下了车,站在我身侧,斗笠下一双眼睛在黯淡的天光里亮得惊人,“静慧师太说过,后山菜园有条小径,通她修行的静室,寻常人不知道。”
我和苏明真对视一眼。苏明真点头:“行,跟我来。”
她把马车赶到更深的山坳里,用枯枝盖了,又撒了把香灰掩盖车辙印。我们三人弃了车,沿着山脚一条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小径,往山里钻。
林晚照走在最前。他脚步很轻,落地无声,对山路似乎很熟悉,偶尔有岔路也毫不犹豫。我跟在他身后,看着他挺直的背,那身青布长衫在晨雾里被露水打湿了肩头,显出几分少年人单薄的轮廓。
他还是个孩子。我心里忽然冒出这个念头。十六岁,本该在学堂读书,在桃花树下吟诗,而不是在这荒山野岭,深一脚浅一脚地逃亡。
“阿姐,小心。”他回身,扶了我一把。我脚下踩到块松动的石头,差点滑倒。
他的手很稳,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。我借着他的力站稳,忽然意识到,这个“孩子”的手心,有比同龄人粗糙得多的薄茧,不止是握笔留下的。
“你在江南……还做过什么?”我问,声音很轻。
他沉默了一瞬,才道:“陈先生教书的束脩微薄,我帮着做些活计。农忙时下田,闲时去镇上铺子里抄书,也……跟着镖局的武师练过几天拳脚。”
他说得平淡,但我听出了话外的艰辛。一个外来的少年,要在一地扎,要读书,还要不引人注意地活下去,其中的难处,可想而知。
“苦吗?”我问。
他侧过脸,晨雾里,我看见他唇角似乎弯了弯:“不苦。能活着,能读书,能等……就很好了。”
等。等什么?等真相?等回家?还是等……我?
我没再问,只是默默跟着他往上爬。山路越来越陡,露水打湿了裙摆,冰凉地贴在小腿上。苏明真殿后,时不时停下来,侧耳倾听山下的动静。
约莫走了一个时辰,天边泛起鱼肚白,我们终于绕到后山。一片菜园出现在眼前,篱笆疏疏落落,地里的菜刚冒出嫩芽,沾着露水,青翠欲滴。菜园尽头,是间孤零零的茅屋,屋顶铺着茅草,窗纸昏黄,透出一点微弱的烛光。
静慧师太的静室。
林晚照脚步停了停,似乎在确认什么。然后他上前,轻轻叩了叩柴扉。
三长,两短,停顿,再三长。
是暗号。
屋里静了片刻,然后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。静慧师太的脸出现在门后,她似乎一夜未睡,眼下有浓重的青影,但眼神依旧清明锐利。她目光扫过我们三人,最后落在林晚照脸上,停留了一瞬,随即侧身:
“进来。”
屋里很小,一床一桌一凳,桌上点着盏油灯,火苗如豆。空气里有陈旧的香火味,还有一股淡淡的、若有若无的药草苦气。
师太掩上门,闩好,这才转身,看向林晚照,声音很轻,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:
“你回来了。”
“是。”林晚照摘下斗笠,露出一张被晨雾打湿的、略显苍白的脸,“师太,我回来了。”
静慧师太走上前,伸手,似乎想摸摸他的头,就像很多年前对那个被抱来的婴孩那样。但手抬到一半,又放下了。她转而看向我:
“宫里的事,知道了?”
“知道了。”我点头,“废太子暴毙,王皇后发疯,秦嬷嬷下狱。师太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静慧师太没立刻回答。她走到桌边,拨了拨灯芯,火苗跳了跳,照亮她脸上深刻的皱纹。她看上去很疲惫,那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疲惫。
“是反噬。”她缓缓开口,声音低沉,“王家用巫蛊之术害人,用风水煞局夺运,用毒药控制人心……这些阴私手段,用久了,自然会遭反噬。只是这反噬,来得比我想象的快,也……狠。”
“可这和‘双生子索命’有什么关系?”苏明真忍不住问,“王皇后发疯时喊的……”
“因为她心里有鬼。”静慧师太抬眼,目光锐利如针,“当年,婉娘怀的是双生子,这件事,王皇后是知道的。她怕,怕龙凤呈祥,怕双生子带来的福运冲了王家的煞局。所以她让王若眉动手,要么弄掉孩子,要么……把孩子变成煞。”
“变成煞?”我心头一寒。
“双生子,一阴一阳,若是用邪术炼化,是极厉害的煞器。”静慧师太声音发冷,“王皇后身边,有懂此道的人。当年若不是你祖父察觉不对,连夜将晚照送走,又将你娘藏进祠堂,用镇煞钱阵护着,你们姐弟俩,恐怕早已成了王家的傀儡。”
屋里一时死寂,只有油灯燃烧的噼啪声。我后背发凉,想起祠堂供桌下那串“洪武通宝”,想起井底那些刻着“见符如晤”的铜钱,想起王若眉看我的眼神——那不是看仇人的眼神,更像是看一件……器物。
“所以,”林晚照忽然开口,声音异常平静,“我活着,对王家来说,就是个威胁。所以我必须‘死’,必须消失在井底。而我阿姐……她活着,但被他们用绝子药、用侯府的亲事、用沉塘,一点点磨掉生气,变成他们能控制的‘煞’?”
他说得条理清晰,冷静得可怕。静慧师太看着他,眼神里有痛惜,也有赞赏:
“是。你们姐弟俩,一个是他们想炼而不得的‘阳煞’,一个是他们已快养成的‘阴煞’。如今王家倒了,煞局破了,反噬自然落到布局者身上。废太子暴毙,是煞气反冲;王皇后发疯,是心魔反噬。至于她喊的‘双生子索命’……”
她顿了顿,看向我和林晚照:
“那是她亏心事做多了,自己吓自己。但这话传出去,对你们不利。现在宫里宫外,不知多少双眼睛在找‘双生子’。你们必须藏好,尤其晚照,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还活着,更不能让人知道,你是婉娘的儿子。”
“可我已经回来了。”林晚照说。
“所以你得换个身份。”静慧师太走到床边,从枕下摸出个布包,打开,里面是几样东西:一张度牒,一份路引,几块碎银,还有一套半旧的道袍。
“这是观里一个云游道士留下的,他前年病死在观里,度牒是真的,年纪也对得上。从今天起,你就叫清风,是我新收的弟子,在观里挂单。”她把东西推给林晚照,“少说话,多做事,别出后山。等风声过了,再作打算。”
林晚照接过道袍和度牒,没说话,只是默默看着。道袍是靛蓝色的,洗得发白,袖口有补丁,但净。
“阿姐呢?”他抬头问。
“你阿姐不能留在观里。”静慧师太看向我,“白云观是王家的产业,现在被盯上了,你留下,反而危险。而且……”
她犹豫了一下,才道:“镇北侯世子递了消息来,说让你去侯府别院暂避。那里是陛下赐的产业,守卫森严,等闲人进不去,比这儿安全。”
赵谨言?他果然递了消息。可让我去侯府别院……
“不行。”林晚照立刻道,“阿姐不能去。”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
他抿了抿唇,脸上掠过一丝挣扎,最终低声道:“我……在江南时,听到一些传闻。关于镇北侯府,关于赵世子……他身上的毒,没那么简单。阿姐,离他远点。”
我心里一动。赵谨言的毒,确实蹊跷。醉骨香是北疆奇毒,连太医院都束手无策,我却能用南疆偏方压制。这方子,是前世在侯府试药时偷学的,可侯府怎么会有南疆的毒方?
“晚照,你听到了什么?”我盯着他。
他摇头,避开了我的目光:“只是些闲话,当不得真。但阿姐,侯府水深,你现在去,不合适。”
静慧师太叹了口气:“晚音,我知道你担心晚照。但眼下,分开藏匿,对你们都好。侯府别院虽非万全之地,但赵世子既然开口,总能护你一时。至于晚照……”
她看向林晚照,眼神严肃:“你既回来了,有些事,也该让你知道了。你娘……留了样东西给你。”
她从怀里取出个小小的油布包,只有巴掌大,裹得严严实实。打开,里面是半本手札,纸页泛黄,边缘有火烧过的焦痕。
“这是你娘的手记,当年她从侯府带出来的。里面记了些东西,关于你的身世,关于林家的秘密,也关于……你祖父为何非要送你走。”静慧师太把手札递给林晚照,神色郑重,“你看完后,烧了,一个字也别留。”
林晚照接过手札,手指抚过封面上娟秀的字迹——“周氏手札”。他指尖有些发颤,但很快稳住了,紧紧攥住。
“天亮前,晚音必须走。”静慧师太看向窗外,天色已蒙蒙亮,山间起了雾,白茫茫一片,“苏丫头,你送她下山,从后山小径走,别让人看见。”
苏明真点头:“好。”
“阿姐。”林晚照忽然叫我。
我回头。他站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,穿着那身过于宽大的旧道袍,身形单薄,但背挺得很直。他看着我,眼睛里有太多情绪翻涌,最后只化成一句:
“保重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我走上前,想替他理理衣领,手伸到一半,又停住。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,像小时候娘对我做的那样,“好好活着,等我来接你。”
他没说话,只是用力点了点头。
苏明真拉开门,晨雾涌进来,带着山间清冽的寒气。我最后看了林晚照一眼,转身,踏进雾里。
山路湿滑,雾气浓得化不开,三五步外就看不见人影。苏明真走在前面引路,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,脑子里乱糟糟的,一会儿是林晚照穿着道袍的样子,一会儿是静慧师太凝重的脸,一会儿又是赵谨言咳血的模样。
“姐,”苏明真忽然低声说,“你觉不觉得,晚照有点……不对劲?”
“哪里不对劲?”
“说不上来。”她挠挠头,“就是感觉……他太冷静了。知道那么多事,突然回来,又突然要扮道士,可他好像……一点都不慌。”
我沉默。确实,林晚照的冷静,超乎他的年龄。那种沉稳,不像十六岁的少年,倒像经历过风浪的大人。
“也许是在外头久了,习惯了。”我说,像是在说服她,也像是在说服自己。
苏明真不说话了。我们又走了一段,雾气渐渐散了,天光透下来,能看见山下官道的轮廓。远处传来马蹄声,很急,由远及近。
“躲起来!”苏明真一把将我拉到路边的灌木丛后。
马蹄声越来越近,不是一匹,是一队。我们从枝叶缝隙里看去,是一队官差,约莫十来人,穿着京兆府的号衣,为首的是个黑脸汉子,腰佩长刀,脸色阴沉。
他们在岔路口停下,黑脸汉子勒住马,四下张望。
“头儿,还追吗?”一个年轻官差问。
“追个屁!”黑脸汉子骂了句,“这荒山野岭,往哪儿追?回去禀报大人,就说人进了西山,八成是躲白云观里了!”
“可白云观是……”
“是什么是?王家倒了,白云观还算个屁!给我搜!观里观外,掘地三尺也得把人找出来!”
官差们应了一声,打马往白云观方向去了。
我和苏明真伏在灌木丛后,等马蹄声远去,才慢慢起身。我手心全是冷汗,心脏跳得厉害。
他们是在找我们?还是找林晚照?或者……找别的什么人?
“姐,咱们得快走。”苏明真脸色也白了,“官差要搜山,晚照和师太……”
“回去。”我转身就往回走。
“不行!”苏明真拉住我,“你现在回去,就是自投罗网!师太既然让咱们走,肯定有安排。咱们先下山,去找赵世子,他或许有办法!”
我挣开她的手,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林晚照还在观里,官差要去搜山,他不能被抓到。
“苏明真,”我看着她的眼睛,一字一句,“那是我弟弟。我把他从江南找回来,不是让他再被人抓走的。”
她张了张嘴,最终颓然松手:“……行,我跟你回去。但咱们得绕路,不能撞上官差。”
我们没走原路,而是沿着山脊,从更陡峭的侧面往上爬。山路难行,荆棘刮破了裙摆,手上脸上也添了几道血痕,但我们没停。
爬到半山腰,已能看见白云观的黑瓦屋顶。观里很安静,没有香客,也没有钟声,像座空观。但后山菜园的方向,隐约传来喧哗声。
“坏了!”苏明真低叫一声,“官差已经到了!”
我们加快脚步,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菜园外。篱笆倒了,菜地被踩得稀烂,静室的柴扉大开,里面空无一人。
只有地上,散落着几页烧了一半的纸,纸灰还是温的。
是那本手札。林晚照烧了它。
“人呢?”我冲进静室,里面空荡荡,床铺整齐,油灯还燃着,像主人只是临时离开。
“别慌。”苏明真蹲下身,仔细查看地面,又走到窗边,推开窗,指着窗外泥地上几个浅浅的脚印,“从这儿走的,往山上去了。脚印很新,不止一个人,是两个人……不,三个。”
三个?除了林晚照和静慧师太,还有谁?
“追!”
我们翻出窗户,跟着脚印往山上追。脚印时隐时现,进了林子后就更难辨认,只能凭着折断的枝条和倒伏的草叶判断方向。
越往上,林子越密,雾气又浓了起来。我们不敢大声喊,只能压低声音呼唤:
“晚照——”
“师太——”
没有回应。只有风吹过林梢的呜呜声,像无数人在低语。
追了约莫一刻钟,前面忽然传来打斗声,还有兵刃相击的脆响。
我心里一紧,拨开挡路的枝条冲过去。林间一片空地上,三个人正在缠斗。
是静慧师太,林晚照,还有一个黑衣人。
静慧师太手里拿着烧火棍,舞得虎虎生风,竟将黑衣人得连连后退。林晚照站在她身后,手里攥着把柴刀,刀尖对着黑衣人,眼神凶狠得像头小狼。
黑衣人蒙着脸,只露出一双眼睛,眼神阴鸷。他手里是把短刀,刀法狠辣,招招致命,但静慧师太的烧火棍总能在关键时刻挡住。
“师太!晚照!”我喊了一声。
黑衣人闻声,动作一滞。静慧师太抓住机会,一棍扫在他腿弯。黑衣人闷哼一声,单膝跪地,但随即手腕一翻,短刀脱手飞出,直射林晚照面门!
“小心!”我扑过去,想推开林晚照,但他动作更快,侧身,挥刀——
铛!
柴刀磕在短刀上,火星四溅。短刀偏了方向,钉在旁边树上,刀柄兀自颤动。
黑衣人趁这空隙,翻身跃起,几个起落,消失在密林深处。
静慧师太没有追,她拄着烧火棍,喘着气,脸色发白。林晚照扔了柴刀,扶住她:“师太,您没事吧?”
“没事。”静慧师太摆手,看向我,眼神复杂,“你们……怎么回来了?”
“官差搜山,我们不放心。”我看着黑衣人消失的方向,“那是谁?”
“王家的余孽。”静慧师太声音发冷,“来灭口的。他们知道晚照回来了,也知道手札在我这儿。”
“手札……”
“烧了。”林晚照接口,语气平静,“重要的东西,我记下了。原本不能留。”
他记得?那本手札不算薄,他这么快就看完了?还能记下?
我看着他,他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有眼底深处,有什么东西沉了下去,像石子落入深潭,不起波澜,却带着千钧重量。
“此地不宜久留。”静慧师太直起身,“官差很快会搜到这儿。晚音,你带晚照走,按原计划,去侯府别院。”
“可您……”
“我自有办法。”她打断我,从怀里摸出个小瓷瓶,塞给我,“这里面是易容的药膏,能用三次。给晚照用上,换个模样。记住,在侯府,少说话,多观察。赵世子……可信,但不可全信。”
我攥紧瓷瓶,还想说什么,静慧师太已转身,朝着和黑衣人相反的方向走去,背影在晨雾里渐渐模糊。
“走吧,阿姐。”林晚照轻声说。
他弯腰捡起柴刀,用袖子擦掉上面的泥土,然后看向我,眼神里有种超越年龄的沉静:
“这次,我跟你走。”
我看着他,又看看静慧师太消失的方向,最终点头。
天亮了,雾气在散去。山下的官道隐约可见,远处,京城的方向,朝阳正从连绵的屋脊后升起,将半边天染成血红色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而我和林晚照的路,才刚刚启程。
第15章:别院客
侯府别院在京城西南的玉泉山下,远离闹市,依山傍水,是个避暑的好去处,也是陛下赏给镇北侯府为数不多的、没被王家染指的产业。
我和林晚照赶到时,已是午后。马车是苏明真从山下村子里雇的,破旧,但不起眼。赶车的老汉收了两块碎银,什么也没问,掉头就走了。
别院门脸不大,青砖灰瓦,两扇黑漆大门紧闭,门口一对石狮子,狮子头被人敲掉了一半,露出里头粗糙的石料。门楣上挂着块匾,写着“静园”二字,字迹遒劲,是赵谨言的笔迹。
我上前叩门。门环冰凉,叩了三下,停顿,又叩两下。
这是赵谨言信里给的暗号。
门开了条缝,露出一张苍老的脸,是个老仆,穿着半旧的褐衣,眼神浑浊,但看人时很锐利。他打量我们,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停,又落在林晚照身上。
“找谁?”
“求见赵世子,姓林。”我说。
老仆没说话,侧身让开。我们进去,门在身后合拢,落闩声沉重。
别院里很静,是那种空阔的静。院子很大,种满了竹子,风一过,竹叶沙沙响,像下雨。一条青石板路通向深处,路两旁是荒了的圃,杂草丛生,看得出很久没人打理了。
老仆引着我们往里走,脚步很轻,踩在青石板上几乎没声音。他带我们穿过两进院子,到了第三进。这进院子更静,正房三间,门窗紧闭,廊下挂着几串风铃,是铜的,锈了,风一吹,发出暗哑的叮当声。
“世子在后头竹林里。”老仆终于开口,声音嘶哑,“你们自己过去吧。”
他指了个方向,转身走了,背影佝偻,很快消失在月门外。
我和林晚照对视一眼。他脸上已涂了易容的药膏,肤色暗了些,眉毛粗了,鼻梁高了点,连唇形都略有改变,加上一身半旧的道袍,看上去就是个寻常的、有点木讷的小道士。静慧师太给的药膏很神奇,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
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竹林在院子后头,很大一片,竹子生得密,阳光漏下来,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。竹林深处有间竹亭,亭里坐着个人,背对着我们,一身素白衣衫,正在……煮茶。
是赵谨言。
他听见脚步声,回头。阳光透过竹叶落在他脸上,脸色依旧苍白,但比上次见面好了许多,至少唇上有了点血色。他看见我,笑了笑:
“来了?”
目光扫过我身边的林晚照,停顿了一瞬,但没多问,只指了指亭子里的石凳:
“坐。茶刚好。”
我在他对面坐下。林晚照没坐,站在我身侧半步远的地方,微微垂着眼,像个小道士该有的恭谨模样。
赵谨言斟了茶,推给我一杯。茶是明前的龙井,碧绿的茶叶在素白的瓷盏里舒展,清香扑鼻。但我没动。
“世子知道我弟弟的事?”我直接问。
他端起茶盏,吹了吹浮沫,啜了一口,才道:“静慧师太递了消息。说你们姐弟要来,让我照应。”
“只是照应?”
“不然呢?”他抬眼,目光平静,“林家的事,是陛下的恩旨,翻篇了。你弟弟既然活着,就该好好活着。这别院清静,没什么人来,你们住下,等风头过了,再做打算。”
他说得轻描淡写,好像收留两个朝廷钦犯的家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可我知道,没那么简单。王家倒了,但余孽未清,宫里盯着林家的人不会少。赵谨言这时候把我们接进别院,是担了风险的。
“为什么帮我们?”我问。
“为什么?”他笑了,笑得有些苍凉,“大概是因为,这世上,能真心实意想我活的人不多。你算一个。我欠你一条命,也欠你……一句谢谢。”
他看向竹林深处,目光悠远:
“林晚音,你知道吗,我父亲临终前,拉着我的手说,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,是你祖父。当年北疆那场败仗,你祖父看出军需有问题,连夜写了密折,托人送进京。可那密折,没送到陛下手里,半路被截了。截折子的人,是我父亲。”
我心头一震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那折子里,不止有王家贪墨的证据,还有……镇北侯府通敌的线索。”赵谨言声音很低,像怕惊扰了什么,“我父亲是被冤枉的,但他没法自证清白。王家拿住了把柄,他压下调査,他替王家背了部分黑锅。你祖父的折子,成了催命符。王家要灭口,我父亲……只能先下手为强。”
他闭上眼,喉结滚动:
“你祖父的死,不是意外。是王家的毒,也是……我父亲的默许。这件事,我查了三年,直到拿到井里那些证据,才拼凑出全貌。林晚音,我赵家欠你林家两条命——你祖父,你娘。如今王家倒了,这债,该还了。”
竹林里很静,只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,和远处隐约的鸟鸣。我握着茶盏,指尖冰凉。
原来是这样。祖父不是病死的,是被人害死的。凶手是王家,但帮凶……是镇北侯。
“你现在告诉我这些,就不怕我恨你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平静得可怕。
“怕。”他睁开眼,看着我,眼神坦然,“但我更怕,你从别人嘴里听到,然后恨我一辈子。林晚音,我父亲做错了事,我认。你要报仇,我这条命,你随时可以拿走。但在那之前,让我把欠你林家的,还清。”
我盯着他,看了很久。他脸色苍白,眼神却清亮,没有闪躲,也没有哀求,只是陈述一个事实。
恨吗?当然恨。可恨谁?恨眼前这个重伤未愈、挣扎求存的赵谨言?还是恨那个已经死了三年、连尸骨都没找全的老侯爷?
“我祖父的尸骨……”我开口,声音发涩。
“在北疆,我父亲衣冠冢旁边,我立了个衣冠冢。”赵谨言说,“等这事了了,我带你去祭拜。还有你娘……井里的尸骨,我让人起了出来,重新装了棺,暂时停在城外的义庄。等你决定好葬在哪儿,我再安排下葬。”
他都安排好了。静悄悄地,把这些事都做了。
我鼻子一酸,差点掉下泪来,但忍住了。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
“王家余孽在找晚照。”我换了话题,“今天早上,有人去白云观灭口,是个黑衣人,身手很好。”
赵谨言神色一凝:“看清长相了吗?”
“蒙着脸。但师太说,是王家的人。”
“王家养的死士,活不露面,死不留名,很难查。”他沉吟片刻,“不过既然动了手,就说明他们急了。你弟弟在这儿的事,瞒不了多久。得尽快给他换个身份,送出京。”
“送出京?去哪儿?”
“江南。”赵谨言看向林晚照,“他在江南长大,那里有基,也有人脉。换个名字,换个地方,重新开始,最稳妥。”
林晚照一直垂着眼,此刻忽然抬头:
“我不走。”
声音不大,但很坚定。
赵谨言挑眉:“留在这儿,不安全。”
“走了,就安全吗?”林晚照反问,语气平静,却带着一股执拗,“王家要灭口,我在哪儿,他们就会追到哪儿。与其东躲西藏,不如留在这儿,等他们来。”
“等他们来?”赵谨言笑了,笑得有些冷,“小子,你知道王家的死士是什么人吗?他们人不眨眼,你这样的,十个也不够他们塞牙缝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晚照看着他,眼神清亮,“但我阿姐在这儿。我不能走。”
赵谨言愣了一下,看向我。我没说话,只是端起那杯凉透的茶,喝了一口。苦,但回甘。
“行。”赵谨言最终点头,“你要留,就留。但别后悔。”
“不后悔。”
竹亭里又静下来。阳光西斜,在青石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风大了些,吹得竹叶哗哗响,像水。
“对了。”赵谨言忽然想起什么,从怀里摸出个东西,递给我。
是个小小的锦囊,杏黄色,绣着缠枝莲,针脚细密,是我娘的手艺。
“这是……”我接过,手指发颤。
“从井里起出来的,和你娘的尸骨放在一起。”赵谨言说,“里面有条手绳,编得粗糙,像是孩子编的。还有张纸条,字迹很稚嫩,写着……‘给弟弟’。”
我解开锦囊,倒出里面的东西。是条五色丝线编的手绳,颜色褪了大半,但能看出编得很用心,只是手法生疏,有些地方松了,有些地方紧了。还有张纸条,泛黄,脆得仿佛一碰就碎,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:
给弟弟。
是我写的。七岁那年,娘教我编手绳,说等弟弟出生了,给他戴上,他平安长大。我编了一条,又一条,总觉得不够好。最后这条,是我最满意的一条,藏在妆奁底层,想等弟弟出生那天,亲手给他系上。
可弟弟还没出生,娘就死了。我也忘了这条手绳。
“你记得这个吗?”赵谨言问。
我点头,攥紧了手绳,丝线粗糙,硌着掌心。我转头,看向林晚照。
他也在看着手绳,眼神复杂,嘴唇抿得发白。我拿起手绳,走到他面前,拉过他的左手。
手腕很细,骨骼分明。我把手绳系上去,打了个死结。丝线褪了色,衬着他暗了些的肤色,不显眼,但仔细看,能看出是条手绳。
“娘说,戴上这个,能保平安。”我低声说,“我手艺不好,你别嫌弃。”
林晚照看着腕上的手绳,许久,才低低“嗯”了一声。他抬起另一只手,轻轻摸了摸那条粗糙的丝线,指尖有点抖。
“阿姐。”他叫了一声,声音很轻,像怕惊碎了什么。
我没应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。然后转身,对赵谨言说:
“我们住哪儿?”
赵谨言指了指竹林另一头:“那边有排厢房,一直空着,我让人打扫出来了。常用度,缺什么跟老吴说,就是刚才引你们进来的老仆。他是我父亲留下的老人,嘴严,靠得住。”
“多谢。”
“不必。”他摆手,又咳了两声,脸色白了白,“我伤还没好利索,大部分时间在屋里静养。你们自便,但别出别院。外头……不太平。”
我点头,带着林晚照往厢房去。走出几步,回头看了一眼。
赵谨言还坐在竹亭里,背对着我们,望着竹林深处。素白的衣衫被风吹得微微扬起,背影单薄,像株随时会折断的竹子。
阳光透过竹叶,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明明暗暗,看不真切。
厢房很净,一应陈设简单但齐全。我被安排在靠东的一间,林晚照在隔壁。推开窗,窗外是片小小的池塘,残荷枯梗,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。
“阿姐,”林晚照跟进来,关上门,压低声音,“赵世子的话,你信几分?”
我转身,看着他。易容药膏改变了他的容貌,但改不了眼神。那双眼睛里,有着超越年龄的审慎和警惕。
“五分。”我说。
“哪五分?”
“他欠林家债,想还,这是真。王家余孽在找我们,这也是真。”我走到窗边,看着池塘里自己的倒影,“但他父亲和我祖父的死,或许还有隐情。他未必全说了。”
“那咱们……”
“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我打断他,“眼下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。你先住下,把师太给的手札内容,仔细想想。有什么不对劲的,记下来,咱们慢慢琢磨。”
林晚照点头,没再多问。他走到自己那间房门口,又停住,回头:
“阿姐,那条手绳……谢谢你。”
我笑了笑:“一家人,不说谢。”
他也笑了笑,左颊那个浅浅的梨涡,在易容药膏下不太明显,但还是能看出一点影子。
他关上门。在窗边,听着隔壁传来轻微的声响,是他在收拾东西。
夕阳西下,天边烧起了晚霞,红得像血,染红了半边池塘。风停了,竹林静了,整个别院笼在一种诡异的安宁里。
我攥紧了袖中的锦囊,里面除了手绳和纸条,还有那两块玉佩——我的,和林晚照的。
并蒂莲,本该同同生,可我们姐弟,一个在阴,一个在阳,一个在明,一个在暗,兜兜转转十六年,才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别院里,系上一条褪了色的手绳。
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,是山下寺庙的晚钟。一声一声,沉重,悠长,像在提醒什么,又像在超度什么。
我闭上眼,深吸一口气。
玉泉山的夜,来了。
小说《昨日明月照今我》试读结束!